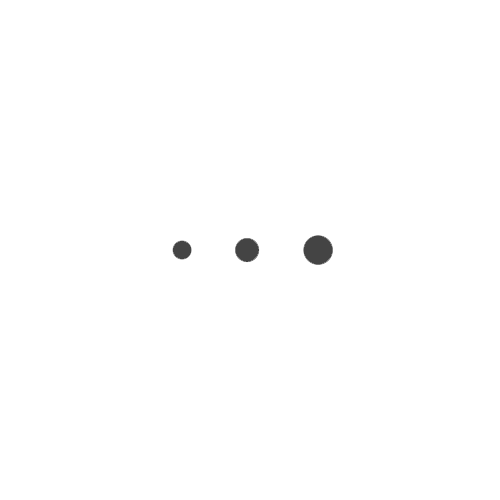「五、四、三、二、一,新年快樂!」我對屋外大叫。
煙花隨即「噼嚦啪啦」爆發,我雙手合十許願——來年生活安穩,來年生活安穩,來年生活安穩。許願的同時,想像着今時今日香港萬家燈火,中環24×7地運作,還在懷緬從未看見繁華盛世、在獅子山遇上的羅文?我祈求來年生活安穩,意味着維持原有的美好,就像保持身體線條、養一組肌肉般,說來不易。
花火很安穩地爆個不停,沒有停歇的意思。我一直看,一直看,一小時後,我在露台叫進屋內:「老公,你來看一下,外面在燒銀紙呢!」他沒有回應,我想他應該正安安穩穩地坐在廁所裏享受着,我沒有打擾他的工事。
我倚在露台那及至胸口高的玻璃圍欄,低頭,萬家燈火,馬路井然,車燈、街燈,延綿導向維港景緻。抬頭遠眺煙花,乾淨無煙的煙花,時而「轟轟隆隆」有重量的大花球,紅綠藍紫,爆發、墜落;時而一二三四五,「噼噼啪啪啪」五顆像彗星般帶尾巴的光波劃破長空,點點星光,無重量,無力感,頹然或優雅,飄散、熄滅。映襯維港夜色,國金,AIA摩天輪,玻璃幕牆巨型「新年快樂」祝賀,渡海小輪閃爍,漁火閃閃逍遙,不及手機屏幕醉人。張開眼、合上眼,也不見漆黑,光點、光線、光面,像熨金般把光紋貼伏在眼球上,單向單面,只見太平,卻不見立體印象。光,成了世界繁榮指標,引領香港衝出國際。
3點了,煙花依舊爆發着。我大叫道:「老公,老公?」但卻沒有回應。我走到廁所門外輕推,門沒有上鎖,只見老公的單丁拖鞋陳屍地上。走到他專用的黑房,推開了門,另一隻右邊拖鞋反轉伏在暗紅燈光下,浸淫在化學藥水刺鼻的酸。懸空的繩索掛起那滿載經歷的黑白相片像淌血般,一滴,一滴,有節奏地彈奏着。
老公不在家?到底去哪了?拖鞋不成雙,相片還在滴水,走得很慌亂嗎?趕着去幽會?電話、訊息都沒有回應,掉低我一個孤伶伶。外面的煙花爆響了一整晚,感覺一切如常。沒辦法,只好等他回來再教訓他。
等。等。等。等。等。
6:04,天未亮,花火像槍砲不聞不問地連珠爆發,照耀得天都光亮,掩蓋醜陋的漆黑,我牙齒「嗦嗦」作響得幾乎磨平了,牆上掛鐘的秒針「噠噠噠」跳動,覆蓋了我的脈膊跳動聲,像坦克車般輾過內心提醒我這一切有發生過。
7:21,理應白天卻依然黑夜,我睜開眼來睜開眼,打開電視,只有藍色的畫面,就像一場鬧劇正在上演。
8:31,天一直沒有光亮,黎明不會來,「世界末日」這四個字在腦海閃過。
等。等。等。等。等。
時間好像停止般,然而天際煙花的璀璨告訴我時間並沒停下來。我不敢關燈,我不敢閉上眼,我害怕失去知覺後會失去自我,失去「我」。
我問:「『我』很重要嗎?」
「當然重要!」
「為甚麼?」
我想了一下,回答說:「因為『我』要見證歷史,見證世界轉動。」
老公還沒回來,又走進他的黑房,那掛起來的黑白照片怎麼可能相隔幾小時依舊在滴水。凝視相片中當年青澀的我,再摸摸如今眼角上皺紋,嘆了一口氣,頓感時光飛逝可怖,卻不及如今時間停頓讓人孤寂心寒。時間似乎停滯了,我不禁大叫:「世界末日呀老公,我要怎樣活下去?世界末日呀!老公,你到哪裏去了?」
突然,在暗紅的黑房中,不知在哪伸出一股溫暖裹着我雙手,我輕聲問:「老公?老公?」
他在我耳邊輕聲說:「甚麼世界末日呀?」然後他從我的頭上卸下虛擬實景眼鏡,黑房的場景影象隨着眼鏡遠去。我半張開口,呆呆的把視線放在老公的眼眸,說不出半句話來。他說:「昨晚我睡前拔了路由器電源,好讓它重啟,你怎麼就在沒有連線下,自己在元宇宙玩通宵?呵呵呵,沒有網絡,你身處的元宇宙就停滯在斷線前的那一刻,這不是世界末日呀!」
我嚇得差點就要哭出來,強忍淚水一頭栽進老公的懷裏,哭笑不得地臉龐塞到他胸口去左右擦着。
黑房再沒有淌血般的水滴聲,從來沒有槍砲聲,從來沒有坦克聲,我的牙齒不可再有「嗦嗦」聲,再沒有羅文「獅子山下」的歌聲,不再有多餘的喧鬧,就連我的脈膊跳動聲幾乎也得消失,只有煙花在永晝下啪啪啪地綻放,彷彿在粉飾太平般提醒我這個元宇宙中一切如常,安然無恙,天下太平。
熱烈慶祝確切落實堅決果斷嚴正執行各項舉措有力推進實現生活安穩重點環節。如今只剩下一種聲音,香港太平了。
借筆
二零二二年一月八日
凌晨四時四十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