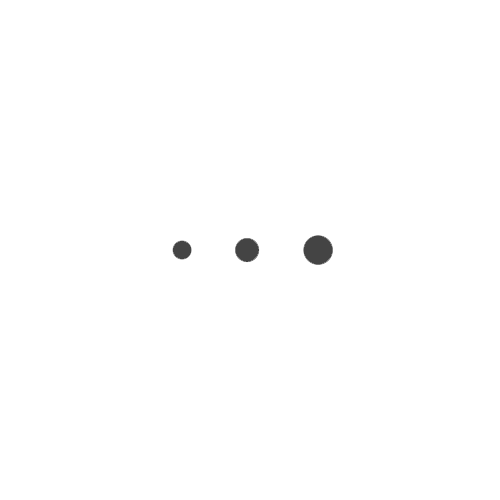第一章 初見
「你好,我是新同事,我叫阿美。」才二十來歲的阿美身材嬌小,一襲金色短髮,聲線爽朗可人,她弓身微前瞇起笑眼來反問對方姓甚名誰時,爽朗笑容從口罩背後穿透出來,一陣甜美如花香般向面前的劉少伯直撲過來。劉少伯一臉與我何干的模樣,未有回應,就像跟陌生人同乘升降機般給自己劃開了安全範圍。他在這部門工作接近二十年,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築起城牆,變得不愛說話,溝通變得矜貴,或許這一切要追溯到前人遺留下來的工作文化背景。
「你好,我是新同事,我叫劉少伯。」劉少伯四十來歲,第一天來到政府檔案處時,在一間擺放了一部大型機器的房間,爽朗地跟坐在機器前的操作員說。
那操作員背着門口,慢慢地轉過頭來,右手顫抖着遞起托一下鼻樑上那圓圓的眼鏡,然後瞥眼向劉少伯點頭,緩緩的右手費勁地指向身旁的座椅上,示意劉少伯坐下,然後又慢慢地把頭鑽回自己的工作上。
劉少伯眼見這操作員的動靜,心中立刻為他起了個名字,樹懶。他後來才知道原來樹懶早在十年前因身體問題,筋骨不靈以致動作緩慢顫抖,走路也要靠拐杖支撐。劉少伯跟樹懶學習操作機器,主要是把其他政府部門的舊文件放進這台如自動販賣機大小的嘈吵機器來複印存檔,每天要處理五千張文件,這是部門要求的目標,一日重複五千次單一的動作,簡直就是鍛練耐性以及單一肌肉的強度。樹懶細心地教導,例如教他修補破爛的文件,先花上一分鐘從膠紙座撕下膠紙,又用一分鐘貼到要修補的位置,先別談論那顫抖雙手的準繩度,能夠眼定定看畢整整兩分鐘貼膠紙的過程,對初來甫到的劉少伯來說,這份工作確是一場相當的考驗。
正因為動作緩慢,說話語氣亦平靜緩和,讓劉少伯聽得舒服,加上劉少伯年輕聰穎,很快便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四十來歲對樹懶來說是年輕了。這對師徒漸漸建立起默契來,偶有談天說地,但也只有待得上司或上司的上司不在場時才能偷聊兩句。要問兩個大男人有甚麼話題呢?由家中瑣事到生活品味,畢竟樹懶未婚,沒有伴侶,而劉少伯已婚,但在家中寥有話語,而且他在外工作多年,對於在政府部門工作多年的井底之樹懶來說,一切都是趣聞趣事。
一天,劉少伯在處理文檔時,一份一九七幾年的報章吸引了他,他笑淫淫地遞給樹懶說:「你看!好東西。」
樹懶慢慢把頭轉動,眼球也隨頭部轉動而移動,盯上那份報紙,笑嘻嘻地說:「不錯呢!你喜歡嗎?」
劉少伯聳聳肩,冷笑一聲,說:「漫畫而已,畫得再裸露都是假的。你看那女的胸脯和體毛,細小的一格漫畫很難畫得傳神真實吧。」他再細心研究,又說:「怎麼七十年代的報紙可以這麼大膽這麼裸露?我中學時代書報攤的鹹書都封上膠袋的。」
樹懶即使戴住口罩,也感受到他嘴角慢慢向上彎,露出帶點邪氣詭譎卻又和譪得感覺到意義深重的笑容,劉少伯只覺這笑容似曾相識,讓他回想起中學時代的一位同學。
第二章 鹹書
「喂,小白,要看嗎?」同學角仔右邊嘴角上揚,笑嘻嘻的模樣,稚氣中帶點邪念,卻又意義深重,一邊跟劉少伯說,右手拇指一邊在虛掩的書包中撩起中二級的中文書,讓劉少伯窺探那本非教科書的書本。
「龍虎……」劉少伯跟着封面來讀,卻被書包中皺巴巴的工作紙阻擋書本全名,而角仔立刻把書包的罅縫合上,好像魔術師有甚麼把戲要先賣個關子般,說:「開卷有益呀!放學一起看啦!」
劉少伯深知無論書名「龍虎」之後的字是「門」還是「豹」,都是學校或老竇老母認為青少年不應閱讀的書藉,這是根深柢固的想法,可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就跟上了角仔的「讀書會」。
放學的時候,連同角仔一行五個乳臭未乾的男生,走到街市上層的平台花園。雖然這平台鮮有人氣,但各人都左顧右盼,眈天望地,誓要尋找一個除了沒有人的地方,更要肯定昨天今天明天甚至永遠都沒有人經過的地點,再來抬頭環視,確切落實沒有街坊能從住家俯視斜視側視能及的位置。一切準備就緒,開封。
角仔戰戰兢兢地從書包掏出一本以濃妝艷抹女人作封面的彩色書冊,小心翼翼地打開透明膠套,一位同學阿成接過,順手摺個整齊,過程緊張得直像手術室醫生把箝子交給護士般,就是未有護士替他抹汗。對劉少伯來說,這個透明膠套正是成年人為免自以為錯誤資訊荼毒青少年所加諸的手段,當然這是他長大了結婚前後才有所領悟。當時當刻在平台花園的劉少伯,只嘲笑阿成把膠套摺疊,卻沒有想過鹹書封套出現前後的意義,或許,這群青少年,打從一開始便接受了鹹書是藏在透明膠套內。
劉少伯不知在哪個時刻完全忘記了還有誰在一起看鹹書,回憶中的那兩個誰就好像漫畫金田一中的兇手般是兩個黑像,或許也沒甚麼關係,反正當日的主角是書本中的女生,不過,在他的回憶裏,就連書本中的人物都是黑像,難道當天他們看那本龍虎豹的主角是黑人女性?
這場男生的讀書會,有人朗讀文章,有人嘲笑相中人蒼老如母,偶有嘻哈大笑,頓有歐陽修觥籌交錯那熱鬧歡愉之感。及後日趨黃昏,加上輕輕雨粉飄降,清爽地落在眾人臉上,也沾上書刊,雖意猶未盡,也只好收拾心情歸去。
畢竟那是禁書,加上早已沾濕了,結果被扔掉到垃圾桶去。書刊丟了,剩下的透明膠套卻被阿成帶回家去。
第三章 雨粉
每當劉少伯遇上雨粉,總會憶起那次失戀後第61日。正因阿美以宛如雨粉般清爽的笑容向他襲來,使他腦中釋放出安多酚和多巴胺,因而激起他年少輕狂的回憶。
這段情除了失戀第61日之外,最刻骨銘心的回憶可算是那年七一回歸假期,當日萬里無雲,藍天碧海,水清沙幼,遍地海星,他倆席地而坐,聽着陣陣海浪,相擁而睡,繼而血脈沸騰,體液交流。海灣無人,即便呼天搶地,也毫無顧忌顧慮,盡情享樂。當天,香港人同熱愛這片土地,熱血沸騰,享受着同一個從東方昇起的太陽,畢竟大家都曬傷了。
感情建基於這片土地上,卻失落於異地,劉少伯在這段感情的尾聲到了國內工作,然後女方因為相處時間太少而提出分手。劉少伯一直懷疑這只是藉口而已,餘情未了的他,念念不忘的他,每天堅持給她短訊。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失戀後第61天,終於收到了她的電話,他把這天寫進了日記簿,然而,這本日記簿直至他遇上阿美,也只有這篇日記。內容如下:
四月,晚上,微微細雨,失戀第61天的我,走到大街上,一個人,沒帶傘,偶爾一襲雨粉撲面,輕輕落在唇邊,舌頭不經意伸伸,一舔,像棉花糖般混和唾液,消失。
地面被雨粉打得濕透,映照道旁昏黃路燈。我享受着,享受這自由自在的空氣,我承受着,承受着那孤獨淒愴的氣息。手機在口袋裏靜俏俏地震動,打斷了這趟旅程的節奏。接過電話,是一位情傷女子的來電,我充滿遐想,二話不說,就要直奔與她會面,安慰。
夜半,三更,走到她家樓下,雨粉仍在飄舞不定,那熟悉公園散發着春草濕氣。遙看,她憂鬱的哀怨籠罩着公園的一角,拿着手機正跟誰傾談着甚麼,處理着甚麼。我默不作聲,在不遠處待着、呆着。
我抬頭細數路燈照射下的雨粉,點點翻飛,隨風飄盪,從陰暗處漸漸淡入燈光氛圍,轉眼又淡出走向黑暗中無痕。淡入,淡出,光轉暗,白到黑,數之不盡的灰階漸層,從來沒有一刀切的消失。
等了一個世紀,她掛了電話,走到我身旁,輕輕牽我手,細訴內心苦澀,苦澀?聽進我耳裏,只不過是跟新歡鬧脾氣而已。
這時,苦澀的人需要一個擁抱,苦悶的人更需要一個擁抱,結果,我倆身體不由自主地去尋找所需要的,擁抱。
時間,讓雨粉在面頰上堆疊,讓感情在擁抱中累積,濕透身體,舌尖濕潤,這是再好不過的藉口轉移去避雨地方,被窩。
被窩中再次完成62天前的例行公事。感覺,跟上次沒有兩樣,她的心,早已鑽到別的被窩去。
這就是青春的迷惘,這就是青春的輕狂,似是困苦中相互安慰,一覺醒來卻各自各忙。
自此,她成了回憶,幾十年來也未曾遇上。
偶爾,一襲回憶撲面,輕輕落在唇邊,舌頭不經意伸伸,一舔,像雨粉般混和唾液,消失。
後記:回憶,總是淡淡然,舌頭不經意伸伸,不痛不癢。
或許過了這個失戀後第61夜,劉少伯才會醒覺,嗅得見「藉口」的味道。
第四章 之痴貓
面對着新同事阿美以笑眼來反問怎麼稱呼時,劉少伯未有回應,心想明明聽得見、聽得懂,怎麼要裝聾扮啞呢?
劉少伯還記得早年在國內工作時,第一天第一句跟國內同事的說話:「前溫屎仇精齋拿?」很可憐的劉少伯,很可憐的普通話呢。對於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來說,只有在小學的普通話堂讀過幾個拼音就當學會了,然後就回歸祖國,到世界工廠工作。幸好,第一天跟第一位溝通的國內同事是懂廣東話的,不然就要寫紙仔了,畢竟「前溫屎仇精齋拿」繁簡體分別不大吧。
劉少伯失戀第61天後很努力學習普通話,多聽多講多溝通,跟國內同事打成一片。結果,他跟一位女生媾得特別投契,朝見口晚見面,共進晚餐後又到工廠附近散步。有一個晚上,他們走到工廠後面一片即將進行工程的爛地,烏燈黑火,只有遠處馬路傳來微弱光線,眼前一個天真可愛的少女,好像未受污染的海洋般清澈,根本不用言語已看穿她的內心底蘊,只要他伸手捉緊,她就屬於他了。然而,她卻看不透他,她不明白他,她還傻乎乎的不知道原來愛是需要了解的,或者反過來說,他看得穿她當刻的思緒,卻看不見她一直以來成長的階梯。這都過去了,重要嗎?原來在劉少伯來說,過去是多麼的重要,要不然他不會到政府檔案處工作,要不然他不會寫下那篇日記,要不然他不會介意她說她小時候最愛「之痴貓」。
回看歷史只有一條脈絡,是由當下的決定組成「歷史」這條時間線。就在這昏暗的土地上,劉少伯正要表白時,她竟然做出了一個決定,她對劉少伯說:「你知道嗎?『之痴貓』巧搞筲的。」劉少伯的普通話經過長時間訓練,大抵明白句子的意思,但就偏偏不知甚麼是「之痴貓」,他右手像珠心算般手指點過不停,盤算着究竟這三個字的拼音,想了一盞茶的時間都想不出來,便要她寫在他的掌心。她一邊用手指在他掌心撩動,一邊嘲笑說:「你怎麼搞的,『之痴貓』都不懂嘛?」老實說,這樣在掌心寫字確實溫暖窩心,要不是這隻貓作怪,他早就表白了,早就相擁床上了。
她邊寫,他邊讀:「機……器……貓……」他心想,甚麼機器貓呀?在幽幽的光線下他露出不惑的表情,她嘲笑道:「機器貓呀,藍色的,有個袋子拿法寶出來。」語畢,劉少伯眼都凸出來,心想:「不是吧……叮噹就叮噹啦,之甚麼痴貓……」
劉少伯臉色一沉,她問:「你怎麼了?我不笑你啦!別生氣了!」
他壓着嗓子問:「你看過孫悟空嗎?」
她笑嘻嘻地說:「有呀,大話西遊嘛。」
他想:「唉……我倒沒聽過大話西遊,是說西遊記嗎?但我是說龍珠呀!」
然後他數了一些陪他成長的人物,飛雲、幽助、小櫻、星矢……她聳聳肩沒有回答,劉少伯在黑暗中流下一滴淚,接着說:「夜了,我送你回去吧!」
第五章 迫婚
「嗄?一半?」劉少伯在元祿壽司跟女朋友討論着。
「我計過了,你夠用的。我們要為將來着想,你未老,可我老了,我想三十歲前結婚。」女朋友氣勢磅礡,續道:「你怎麼都要一起儲,最多我儲大份點,兩年後有三十萬就可以結婚。你知道嘛,現在我做醜人,我都是為你好的,我是為我們將來好的。到結婚生仔後,到時你自然會多謝我的!」
女朋友的這段說話,聽在劉少伯耳裏難聽過粗口。她還補了一句:「無問題啦?那就下個月開始開個聯名戶口。」這刻,他可以拍枱然後一走了之,但他沒有這樣做; 他可以把自己被迫婚的感受說出來,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可以跟她討價還價,但他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默默承受,他以為這是為她好為自己好,他以為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但其實沒有解決過任何事情,只是讓事情繼續發生。
兩年後,一眾親友送來祝賀,他默默接受。而婚後生活,在家中他永遠沒有說對說話因而變得鮮有話語,把內心對外的那口井用木板封上了,有如鹹書被透明膠套包裹似的,只有外表卻看不見內頁底蘊。不過,他做了一件他認為對的事情,他悄悄地做了結紮手術,把輸精管紮了起來,以免禍及下一代。
要怪,就怪當日在元祿壽司沒有作出其他決定,結果任由對方為自己作出安排、擺佈。
婚後五年?八年?好像是五年,她要他考政府工,因為薪高糧準,結果,他進了政府檔案處工作。
第六章 輪迴
樹懶即使戴住口罩,也感受到他嘴角慢慢向上彎,露出帶點邪氣詭譎卻又和譪得感覺到意義深重的笑容。
劉少伯問:「你笑甚麼?你笑得很詭異呢!」
樹懶慢吞吞地說:「我來問你,云云鹹報當中,被選出來的這一張能夠永久保存成為歷史,你知道為甚麼嗎?」
「要選當然選最鹹啦!」
「呵呵呵,聰明!所以被記載的歷史都是被篩選過的。」
劉少伯未完全領會,還在細意嘴嚼時,翌日,樹懶突然提早退休,沒有先兆,沒有通告,沒有討論。是人心惶惶,抑或各自各忙,反正再也沒人提起樹懶,說到底,任何形式的話語都變成了罪惡的根源,寧願不說話,作一枚滑輪自我空轉,也不願成為下一顆被換掉的齒輪。
幾十年後,阿美遇上下一位新同事時,就和劉少伯跟她初遇時一樣,露出一臉與我何干的模樣。
齒輪,仍然在運作。
借筆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
晚上十時四十分